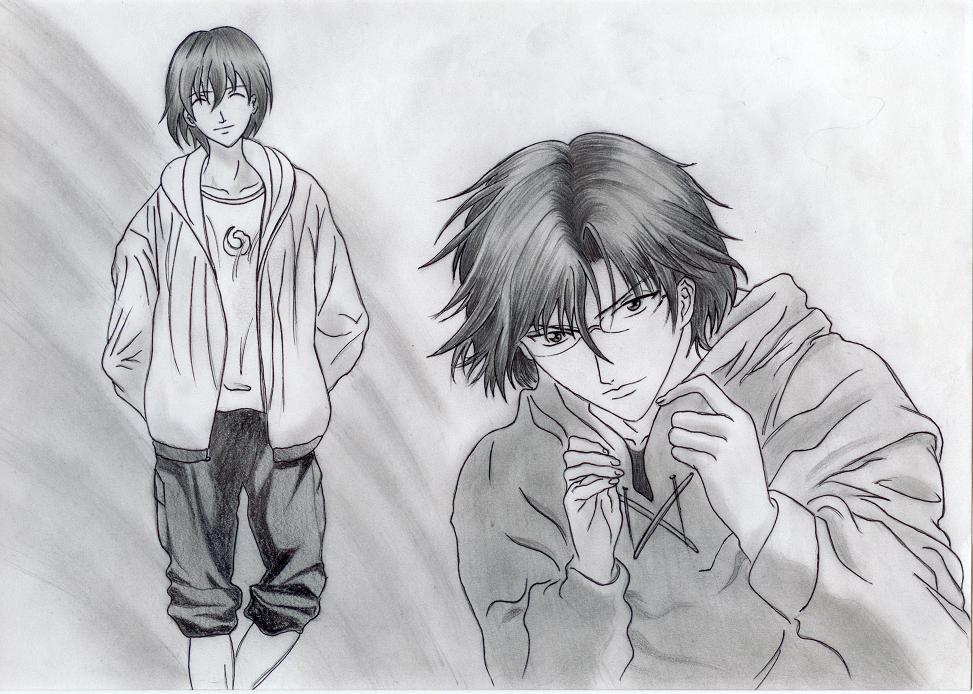转载自:http://home.wangjianshuo.com/cn/
前几天晚饭间,老华组织在座的12个人玩一个猜数字的游戏。。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每人给出一个从0到100之间的数字。把所有人的数字求算术平均值。谁选的数字最接近这个算术平均值的2/3,谁就赢得整场游戏。
这是个很有趣的游戏,建议大家每个人都再仔细读一下题,想一想,试一下?
选一个数,写一个理由,然后再往后看。
分析一下过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游戏里的每个人。如果每个人都是真的随机的选择的话,大家平均值应该在50左右。50的2/3应该是33.3,对吗?很多人都写了33.3。(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步)
不过多想一步,如果你写了33.3,难道其他的人不会想得和你一样,也写33.3吗?如果这样,你应该写22.2。如果继续想下去,大家的平均值应该越来越小,就是这样。。。
50
33.33333333
22.22222222
14.81481481
9.87654321
6.58436214
4.38957476
2.926383173
1.950922116
….
最后,把问题想得非常地复杂的人的答案是0。
这是我们那天的结果
30
98.16
32
50
12
33.3
22
8
8.2
18
28.68
37
所有的平均数:31.445,它的三分之二是20.96333333。选22的人获胜。
世界不是由天才创造的
老华的很多次游戏表明,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体,最终的获胜的数字,都在22左右徘徊。群体决策的结果和天才的想法总是有些格格不入。 这个游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由天才决定的。在众人决策的过程中,赢得游戏的人,都是比别人多想一步的人,而不是多想两步或更多步的人。
游戏中的人
这个游戏里面,选择不同的数,或许就代表了不同的人。
先说选超过66.67 的人。在开始游戏的时候,我悄悄对Wendy说,“肯定不会有人选超过66.67的数字的,要是谁要是写了,一定是没动脑子的”。就算是所有人都写100,获胜的数字也才66.67。结果出来,第二个报出的数字就是98.16。我窃笑。他解释写这个数字的原因是因为没听清楚题。慢着,先别就这样放过这个现象。在现实社会里面,没听清楚规则的人不是比比皆是吗?比方说,做产品的人认为质优价廉用户就会买,而实际上,花高价买差产品的人大有人在,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用户都和和业内人士有一样的判别力,一样的了解规则,对吗?
再说选0的。或许这个结果很多人想都想不到,但老华组织的游戏里面,几乎每次都有选零的,而且越理性的群体,选零的比例越高。比如微软研究院30个人里面高达3个人选零。选零的人,沉浸于自己对世界了解的快感中,却知之者甚少。很可惜,在每次游戏里面,比一般人想一步的人就不多,想两步的人更少,经过重重地归迭代到达0的最终境界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只好轻叹一声,说,你是天才,但是你赢得不了游戏。或许原本他们在写0的时候,本来也就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赢得游戏,而他们就是用这种近似自杀的方式向世界宣称,“我放弃获奖,因为我是天才。我可以接受没有奖励,但我不能接受大家不认为我聪明”。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天才的理论有机会向每一个参与者传播,让他们理解,跟随天才的选择,说不定他还有一线获胜的机会,不过让每个人了解,从古到今就不曾在天才在世的时候实现过。天才不是疯了,就是穷困潦倒。
然后我们来说选33.3的。他们是正常的,平凡的人。就像数以百万计的洗发水的使用者或者报纸的阅读者一样,再正常和普通不过。在明白无误的规则面前,按照规则办事,用思考指导行动,却不多想更多。33.3的人是社会的大多数,在他们前面,有引领世界的0和推动世界的22;在他的后面,有大量的选择随机数的更平凡的人。是33们,奠定了这个社会的基调。
再说赢得游戏的22。他们也遵循规则,但是比规则前进了一步,不多不少,刚刚好一步。他们提出的方案让大多数人(33)感觉的有道理,却不像天才(0)提出的解决方案那么晦涩难懂。我们假设,如果布鲁诺要是发现一个新的号称是绕地球旋转的星星或许能为他赢得终生的荣誉和财富,但如果走得像推翻地心说,宣扬日心说那般的接近真理,得来的就是8年的监禁和熊熊的烈火了。
社会上除了这些种类,还有很多,在游戏里也在出现。比如说选50 的。他在公布答案之前就解释说,“我知道这个数字肯定会非常小,趋近于0,而我就是想说一个大一点的数字,把平均值拉大,看看是会不会左右游戏的结果”。这叫做“搅局的”或者说“损人不利己”的。现实社会里面有吗?大有人在呀。
天才的悲哀就在于,他搞懂了规则,却没有搞懂人。他自己想明白了,就想当然的以为别人也会想明白。他不但错误的忽略了只想到33的人的存在,更忽略了没有思考的,或者存心不按规则玩的人的存在。毕竟,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只有天才的世界。
最后说一说8.2,就是我了。我对8.2的分析是,这个人有一点点天才的倾向,却又不能像选0的天才一样潇洒的放弃冠军的奖励;他希望赢得游戏,却又过高的估计了大众思考的步伐; 8.2被天才斥责有太多功利心,却被22嘲笑过于“自作聪明”,算是一个摇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人。自嘲一下罢了。
天才的选择
对于这个社会,必然有看得比别人稍微透彻些的,离真理更近些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天才吧。这些已经窥探到天机的天才,在现实世界里面,选零还是选22,这是个问题。
选零,就注定了要放弃大多数人的认可。这认可可能是名声,可能是钱。选零的人,适合当教授,适合当评论者,不合适自己来做商业。
如果你本来想选0,却又为了迎合大众选了22,就注定了你要伪装的傻一些,要被业内人士批判,会被选0或者8的人认为不紧跟潮流。大家看一看现在大凡成功的公司,从美国的软件业网络业巨头们,到中国的门户和成功网站,哪个躲得过选0的人的指指点点?或者说,选22的人是易中天,会用通俗(甚至有些错误)的方式讲史,而选0的人就是严肃的历史学家。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和热门网站,在大众和同行两个世界里面有完全不同的声名,大多是因为这样。
没有选0的人,这个世界何以进步?选零的天才们艰难的拖着这个世界前行。我对他们表示敬佩。只可惜,他们获得的只有一小部分人的敬佩。对于选22个人,帮助了无数选33的人改善了生活,他们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没有22,世界怎么可能从33过渡到更小的数字去呢?我对他们也表示尊敬。
世界毕竟不是由天才创造的。
P.S. 好了,下面是包括你在内的三十个人的结果。看看平均值是多少?在现实中,你又会选几呢?
| xiaobao: | 18 | 2006-09-27 10:17:27 |
| 孙秀平: | 44 | 2006-09-28 12:42:07 |
| bluedevils: | 28 | 2006-09-28 01:09:11 |
| 张甜: | 56 | 2006-09-28 05:30:01 |
| 22: | 33 | 2006-09-29 12:17:45 |
| blkmaomao: | 49.8439 | 2006-09-29 01:41:44 |
| 65: | 65 | 2006-09-29 01:43:38 |
| chinaboy: | 20 | 2006-09-29 03:13:51 |
| QQ: | 50 | 2006-09-29 03:27:08 |
| ellen.cai: | 62.3333 | 2006-09-29 03:34:40 |
| thinXer: | 11 | 2006-09-29 03:58:22 |
| Fire: | 30 | 2006-09-29 07:45:45 |
| sun: | 33 | 2006-09-29 11:59:42 |
| whwh: | 32 | 2006-09-30 12:18:15 |
| 李金达: | 66 | 2006-09-30 01:28:08 |
| sb: | 2 | 2006-09-30 05:13:44 |
| kang: | 10 | 2006-09-30 06:20:17 |
| 胡光: | 20 | 2006-09-30 08:52:22 |
| firefox: | 24 | 2006-09-30 11:09:31 |
| 汪笋兮: | 33 | 2006-09-30 11:23:17 |
| : | 23 | 2006-09-30 08:32:28 |
| waying: | 17 | 2006-09-30 11:51:50 |
| cd: | 3 | 2006-10-01 03:33:22 |
| 任帅: | 0 | 2006-10-01 01:12:57 |
| 王大璋: | 13 | 2006-10-01 05:56:15 |
| dont: | 22 | 2006-10-01 10:54:17 |
| burt: | 68 | 2006-10-02 12:25:29 |
| zhaofeng: | 66 | 2006-10-02 09:47:35 |
| : | 25 | 2006-10-02 10:01:21 |
| 姜真钦: | 22 | 2006-10-02 11:11:40 |
| Average: | 31.53924 | |
| 2/3 of Average: | 21.02616 | |
| Winner: | dont | |
| Winning Guess: | 22 |
更新 2006年9月9日
注一: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游戏的全貌,我把更多的结果,包括前100个人,200个人,和1000个人的结果公布出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很有趣,结果都在21到22之间。
注二:每个人对这个游戏都有自己的分析,无论每个人得出的结论如何,觉得有所收获就好。我们谁都不能断定别人看到同样的游戏,甚至同样的分析,可以领会同样的东西(我们不等再当一次0,或者33或者98了)
注三:这个游戏来自老华的启发。老华在很早以前就曾经也写过这个题目,《世界不是由天才创造的》,并且更进一步用《木桶定理》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很有道理,推荐大家去读。
附录:木桶原理杂谈
转载自:http://blog.donews.com/henryhwa/archive/2005/12/16/660337.aspx
学过管理学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木桶定理,就是说一个木桶能盛下多少水,不是由组成木桶壁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而是由最短的一块木板来决定的。
这条定理非常形象,也非常浅显易懂。过去,我们常常把这条定理使用在单个组织或者个人的身上,鼓励组织或者个人要综合发展,要均衡发展。其实,因为社会化大分工和领域细分的存在,使得具有专业特长的组织或个人还是由其存在的空间,其他不足的地方可以通过外包或者与他人配合的方式弥补。但是我们把视野放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从整个社会和整个产业的角度出发,木桶定理才能真正彰显其价值。
我们就拿整体的计算系统对木桶定理来做了演示:
| 计算单元 | 计算效率 |
| CPU | Intel Pentium4的主流机型达到3000MHz |
| 主板内存 | 主流底板的前端总线频率可以达到533MHz或者800MHz,内存的主频在333MHz或者400MHz |
| 硬盘 | 主流SATAII硬盘有7200转/分钟, 最大传输速率达到3GB/S |
| I/O | USB 1.1传输速度为12MB/S, USB 2.0为480MB/S, IEEE1394为400MB/S~1GB/S |
| 人机界面 | 普通人平均每分钟阅读3K-4K的文字信息量,输入0.2K文字信息量 |
| 个人计算 | 一个勤奋的知识工作者平均每天阅读100份邮件和网页,书写30份邮件或文档,总共文字信息量在500K以内,折合工作效率是1K/分钟左右 |
| 小组计算 | 平均每天全组性质的沟通少于1次,组内成员相互之间的沟通同样非常少。一个由N个人组成的团队工作效率往往小于N倍的个人效率(我们把这个比率叫做μ)。 |
| 企业计算 | 在企业中,大部分员工不知道企业的发展状况,不知道企业其他组织的状况。在企业范围中的μ值往往和企业的大小成反比。 |
| 社会计算 | 处在布朗运动阶段,虽然有一些的基本规律可循,但是整体上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 |
比如说在个人电脑中,有经验的攒机族从来不相信那些正牌厂商在整机广告中大大标出的CPU的主频速度,因为他们知道一个电脑中,CPU是最长的一块板,主板不快,内存不大,显示卡不快,硬盘不快都没有用。那些标了奔腾4主频3.0G,但只卖4-5000元的机器,就象是汽车的发动机绑在了自行车轮胎上,跑也不会跑的太快。
发明GUI的伟大之处,不仅仅给用户提供了一个直观,形象的界面,更重要的是把人机界面从80X25的字符界面给解放出来,形成了640*480的图形界面,大大提高了人机界面的效率。当显示器尺寸从14寸,到15寸,17寸,甚至19寸,显示分辨率从640*480,到800*600,1024*768,甚至1600*1200,人们在获得更大可视面积的同时,也可以大大提升人机交流的效率。
微软之所以伟大,倒不是仅仅因为创立了一个市值全球最高的软件公司或者产生了一个世界首富和几千个百万富翁,而是因为他和其他业界同仁(如Intel)一起实现了30年前的梦想“每个家庭每个办公桌上都有台电脑”。在那个年代,计算机不仅昂贵,而且非常难于使用。计算机使用者在当年等同于专家教授,等同于经过长期训练的专业人士。而现在计算机的使用者已经从牙牙学语的稚童到白发皓首的老人,变成了一个类似与家电一样的产品。计算机使用面的扩大和使用难度的降低,大大扩大了计算机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这其中,微软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对提升“个人计算”这块短板功不可没。
举了这么多例子,我们可以得出那些结论呢?
- 在整个计算系统中,同样符合木桶定理。在个人电脑中,决定整体系统性能的不是CPU的主频速度,而是内存,硬盘等短板。在个人计算中,决定整体系统效能的不是机器性能的高低,配置再好的电脑在个别领导手中也就是台打字机,在程序员手中就是征服世界,创造财富的利器。在整体计算系统中,小组计算是比个人计算更短的板,企业计算更差,就更不用谈社会计算了。
- 要提升整体系统的效率,我们要关注在系统中最短的一块板。比如说,我们关注的领域是个人电脑的整体效能,那大家就要多关注硬盘的速度,在笔记本电脑中,还要关注电池的持续时间,因为这些是系统中的短板。如果我们关注的领域是个人计算,我们要关注人机界面的效率和软件的易用性及学习成本,这是最短的板。在小组计算中,最短的板是小组成员使用电脑的共同意识和水平,决不是个别高手和大拿的水平。
- 关注最短的一块板,能带来很大的效益。这种效益不仅仅是整体系统效率的提升,而且能为投资和解决这块短板的人带来巨大的效益。微软的成功就是因为大大提升了“个人计算”的效率和成本,同样Intel的成功不是因为持之以恒的刷新CPU的主频,而是因为坚持不懈的遵守“摩尔定律”,使得计算成本持续大幅降低,这是系统中的短板。
- 将来的机会在什么地方?一定还是系统中的短板。微软把个人计算这块短板提升到了一种极致,那对其他人来说,可以关注更短的板,如小组计算,企业计算甚至是社会计算,在这些领域还许许多多可以提升的领域。比如在小组计算中,虽然早就有了Exchange,Notes等小组计算工具,但是Groove,WSS照样有很大的机遇和发展前途。这些平台关注的焦点,强大的功能在于其次,而如何更加有效的提升小组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以及平台的易用性将成为这些平台的主要特性。
- 越希望成为行业的领袖越应该关注整体系统中最短的板。社会计算是目前最短的一块板。整个社会由于缺乏共同的沟通交流平台和一致的利益驱动机制,使得人类社会的大量资源和能量在无序的布朗运动中消耗掉了。而互联网的出现,为人类提高整体社会计算效率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剩下的事就是你如何发挥想像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