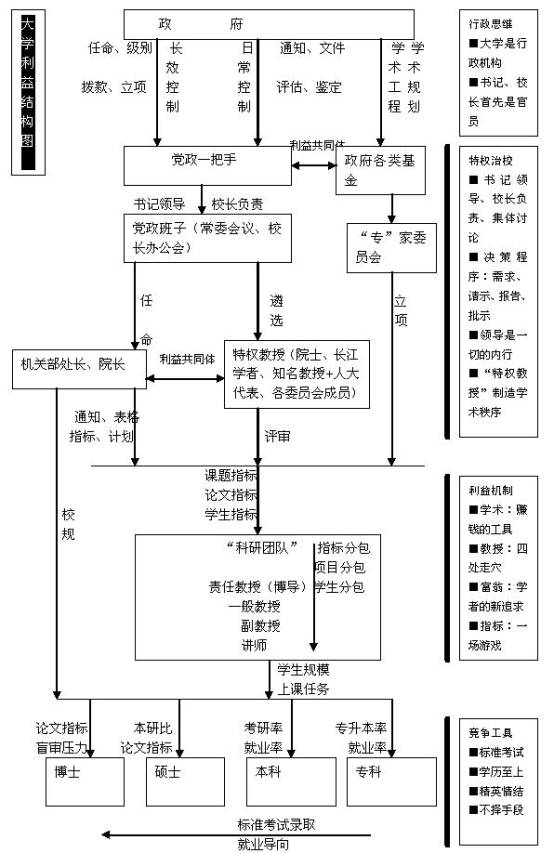这个世界是由不同的规则构成的。当两个相信不同规则的人碰在了一起,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比方说,跨国公司天天面临的就是国际的规则和中国的规则的冲突,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问题。
我和泥水匠的故事
三年前,我装修房子,请了一个包工头,他带着一帮子人进场干活。其中有个四十岁左右的泥水匠,负责贴瓷砖。他手艺很好,做工不错,就是脾气差了点,我们总是合不来。他总是瞅空就奚落一下我,还把工地搞得乱七八糟,让我极为光火。
当时我正受优质的客户服务理念的影响,认为服务业的人,无论是技术工程师还是泥水匠,都应该以客户为中心,千方百计让客户满意。这个泥水匠怎么就一点没有客户的观点呢?我试图摆事实讲道理,让他提高“客户服务”水准。显然,所有努力均以惨败告终。
“这个人怎么连客户至上的观念都没有”,我愤怒的打电话给包工头,让他换掉这个泥水匠,而包工头以“中途换人影响工程质量”为由,一直就没有换。
终于有一天,我经人指点,才恍然大悟。原来,世界上除了我的这一套规则,还有另外一套。不了解游戏规则的恰恰是我。
结果,我给了他50块钱,感谢他这么多天帮忙,夸他活儿做得不错,让拿钱他自己买烟抽。从此,这位古怪的泥水匠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对我好得不得了,处处替我着想,快乐地完成了后来的工程。我自己都觉得好笑,难道就是这50块钱?就这么简单?
到底是谁不了解规则
三年了,这件事情我还记得。泥水匠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做事要讲人情味,“把我请到你们家来干活,连包烟都没有,还想让我给你好脸色看?”这个规则简单直白,当时我就是还不懂他的规则。
两个规则,用你的规则,还是我的规则
当两个规则冲突的时候,到底用谁的规则呢?
如果我坚持我的“客户至上”的规则,我完全可以辞掉这支包工队,找百安居这样按客户的规则玩的公司,我的确是坚持了我的规则,但是付出了两倍到三倍的价钱。结果是,我输。
如果泥水匠坚持他“东家买烟天经地义”的规则,他永远只能拿百安居一半不到的工钱,并且永远是个没有前途的泥水匠。而如果他能够适应客户的规则,放弃自己坚持的东西,或许他可以拿到高一倍的工钱,而不仅仅是多50块钱。
这那个案例里面,我放弃了我的规则,适应了他的规则。我赢,泥水匠输。也就是说,当两种规则发生碰撞的时候,先做出改变,适应对方规则的一方,更容易获得利益。
关于规则的游戏
以前微软有一门叫做《情景领导》的课程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游戏,就是关于不同的规则的。游戏里面,四个人一组,分成了很多个小组,开始打牌。每个人得到一张打牌规则的说明。每个组赢的人,会到顺时针到下一个组继续游戏。在游戏的全程中,不允许任何人说话。
游戏的秘密就在于,每一组之间的规则都是不一样的,而大家都以为每个人的纸上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比如有的组是A最大,有的组就变成3最大,还有的组规定第一个出的那张牌就是最大的。当在一组赢的人到达下一组的时候,这一组的其他三个人手里的规则其实和他是不一样的,他却不知道。在新的组里,他的牌技越高,输得就越惨,就输得越莫名其妙。
直到两轮以后,聪明的人才会逐渐发现,原来规则是不一样的,三轮以后才能慢慢了解这一桌的规则,并学会用新的规则打牌。而脑筋死一点的人,过了几局还没想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牌明明比别人大,其他人却直接就翻了过去,自己失去了发牌机会。
我很喜欢这个游戏。它和现实社会何其相似。一个人,一个公司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还认为规则还是一样的,就大错特错了。而更不幸的是,真实的世界里,连有一张告诉你游戏规则的纸都没有。
中国规则和西方规则的碰撞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很容易坚持按西方的玩法来玩,指指点点,觉得中国很多地方不符合国际惯例。对中国的商业规则,质量水准,甚至到交通规则,都颇有微词。但准确地说,中国不是没有规则,只是没有写下来的规则,没有西方人看得懂的规则,甚至有的时候,不按规则办事本身就是一种规则。这个时候,如果按照全球通行的做法来做,不是不可以,就是要付出高得多的成本,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按国际规则做事情的公司本身就是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比如老冒曾经提到一个朋友坚持在中国办了一间收天价服务费的室内设计公司,做出来的也是国际水准的东西,结果生意好得不得了,因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环顾四周,能够按他们的标准设计的公司,就这么一两家,别无选择.
对于中国的公司,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中国和国际规则接轨是迟早的事情(虽然这比我们想象的以十年计的速度要慢一些),是固守着自己的“潜规则”,还是主动适应国际的规则,就是一个问题。我看到的情况是,主动把标准提高(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商业准则和专业程度),可以获得比成本的提高高得多的回报。用时髦的词来说,那个地方就是蓝海。比方说,我看到的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室装修,多数用的都是贵得让人咂舌的一家香港公司。有什么办法呢?谁让跨国公司不愿意降低标准,所以要付那么高的价格,而本地公司却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无法享受那个价格呢?
规则的冲突和融合
在这个两个规则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冲突和碰撞的时代,谁先适应了对方的规则,谁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高标准的一方如果不降低标准,将会付出比同等公司高得多的成本;低标准的一方,如果主动改变自己,在这个冲突的时代,成本提高一半,价格就有提高一倍的空间。
随着持有不同规则的双方不断的冲突、适应、改变,最终,规则的融合就完成了。而这种规则冲突的时代,却正是有头脑的商人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